(完)三年前,总裁母亲用一千万让我离开总裁
我是夏棠,曾为救弟弟的命,收钱离开了我最爱的人。
三年后我成为顶级设计师,他已是商业帝国掌权者。
他母亲再次递来一千五时,我收下捐了。
当他发现真相将我逼到墙角,我亮出手机里的公司估值:“陆总,现在我的时间很贵。”
01
拍卖厅的水晶灯晃得人眼睛疼。
我捏着18号牌,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。台上正在拍卖一副十九世纪的欧洲油画,举牌者寥寥。这种金融慈善拍卖会,真正的交易都在台下。
“接下来是第37号拍品,由新锐设计师夏棠女士捐赠的珠宝套装‘逆光’。”
我微微坐直身子。
聚光灯打在深蓝色天鹅绒展台上,那套以破碎晶体为灵感的项链与耳饰反射出冷冽的光。主持人介绍着我的设计理念和近期获奖情况,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恭维。
“起拍价,三十万。”
“三十五万。”
“四十万。”
“五十万。”
竞价平稳上升。这套作品市场估价在八十万左右,慈善拍卖通常会溢价。我垂眸看着手中的拍品册,心里计算着今晚的募捐总额能帮基金会多建几间音乐教室。
“一百万。”
低沉的声音从第一排正中传来。
拍卖厅安静了一瞬。
我抬头,看见那个熟悉的背影。剪裁完美的黑色西装,后颈短发利落干净,举牌的左手腕上,一块铂金表盘在灯光下闪过冷光。
陆沉舟。
三年不见,他已从陆家那个需要隐忍的继承人,变成了掌控整个商业帝国的总裁。财经杂志上常见他的专访,标题总离不开“年轻”、“铁腕”、“扩张”这些词。
“一百万第一次。”主持人声音微颤,“一百万第二次——”
“一百二十万。”后排有人加价。
“一百五十万。”陆沉舟的声音没有起伏。
无人再举牌。
槌落定音。
掌声响起,他微微侧头向众人致意。棱角分明的侧脸在镜头下一闪而过,淡漠得像是刚拍下一支笔,而不是一套珠宝。
我移开视线。
中场休息时,我端着香槟杯站在露台边缘。六月的夜风带着城市的热气,吹散了拍卖厅里的香水与雪茄混合的味道。
“夏小姐的设计很特别。”
我转身,对上一双含笑的眼睛。说话的是今晚的主办方代表,姓陈,四十岁上下,笑容恰到好处。
“过奖了。”我礼貌回应。
“陆总刚才高价拍下您的作品,看来对珠宝收藏颇有兴趣。”陈先生意有所指,“不如我引荐你们认识?他对年轻设计师一向支持。”
我还没开口,露台入口处传来脚步声。
几个人簇拥着陆沉舟走进来。他正听身旁一位银发老者说话,偶尔点头,目光扫过露台时,在我身上停了半秒。
毫无波澜的半秒。
就像看见一个陌生侍者。
陈先生已经迎上去:“陆总,正好向您介绍今晚的设计师,夏棠小姐。她的作品您刚才已经收藏了。”
陆沉舟看向我。
距离三米,灯光昏暗,但我能看清他眼中那片深潭。三年前那片会为我燃起火焰的深潭,如今结了厚厚的冰。
“设计不错。”他简短评价,像在点评一份财报。
旁边有人笑着接话:“陆总对艺术品的眼光一向精准。说起来,陆总年轻时的眼光应该也不错?听说您大学时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初恋?”
空气微妙地凝滞。
问话的是个年轻投资人,显然想拉近关系,却不知触到了什么禁区。陆沉舟身边几位老友表情都有些微妙。
陆沉舟晃了晃手中的威士忌杯,冰块叮当作响。
“年少轻狂。”他声音平淡,像在说别人的事,“一场错误而已。”
露台安静了几秒。
随即有人打圆场,话题转向了最近的股市波动。陆沉舟被众人簇拥着往里走,经过我身边时,带起一阵熟悉的冷冽木香。
还是那款香水。
我仰头喝完杯中最后一口香槟,酸涩的气泡刺激着喉咙。
陈先生尴尬地试图安慰:“陆总他……”
“没关系。”我放下杯子,从手包中取出名片递给他,“陈先生,下周我们品牌有个新品发布会,欢迎赏光。先失陪了。”
转身时,我的高跟鞋踩在露台的石板地面上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一步,两步,三步。
我没有回头。
所以我不知道,在我离开后,陆沉舟从拍卖厅的落地窗边转过身,目光穿过人群,久久落在空荡的露台入口。
他手中那杯威士忌,一口未动。
---
拍卖会结束已是深夜。
我站在酒店门口等代驾,手机屏幕亮着,显示订单还有三分钟到达。晚风吹起我耳边的碎发,我伸手拢了拢。
黑色宾利无声滑到面前。
后车窗降下,露出陆沉舟的侧脸。他看着我,眼神在夜色中看不真切。
“上车,送你。”
“不必,我叫了车。”我晃了晃手机。
“取消了。”他语气平淡,“这个时间,这个地段,你要等至少半小时。”
他说的对。金融区的深夜,代驾司机都不愿接短单。
我沉默两秒,拉开车门坐进去。
车内弥漫着和他身上一样的冷冽木香。司机升起隔板,封闭空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。车辆平稳驶入夜色,窗外的霓虹流光般倒退。
“什么时候回国的?”他问。
“三个月前。”
“设计做得不错。”
“谢谢。”
对话干涩得像在履行某种社交义务。我看向窗外,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手腕上的细链——那是我自己设计的第一件作品,廉价银链上挂着一小块不规则水晶。
“还戴着这个。”他的声音突然靠近。
我猛地抽回手,才发现他不知何时倾身过来,距离近得我能看清他睫毛的阴影。
“旧东西,习惯了。”我把手收到身侧。
陆沉舟靠回座位,忽然笑了。不是愉悦的笑,而是一种带着冷意的弧度。
“夏棠,你还是老样子。”他说,“把不值钱的东西当宝贝。”
我转头看他:“陆总倒是变了很多。以前你可不会花一百五十万买‘错误’的东西。”
空气骤然凝固。
他的眼神沉下来,那种审视的、剖析的目光,像是要把我整个人拆开重组。三年前,这样的眼神会让我心跳加速。如今,我只觉得疲惫。
“停车。”我说。
“还没到——”
“停车。”
车在路边停下。我推开车门,夜风灌进来。下车前,我回头看他。
“陆沉舟。”三年后第一次叫他的名字,“那套‘逆光’,设计理念是破碎的东西也能反射光芒。但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,再亮的光也照不回来。”
我关上车门。
宾利在路边停了很久,才重新驶入夜色。
我站在人行道上,看着它消失在街角,然后从手包深处摸出一枚旧硬币。三年前分手那天,我把他送的所有东西都还了回去,除了这枚我们一起在游戏厅赢的纪念币。
当时他说,等我们老了,要拿这枚硬币给孙子讲故事。
我把硬币抛起,接住,紧紧攥在手心。
金属边缘硌得掌心生疼。
远处,代驾司机骑着折叠电动车出现,车头灯在夜色中划出微弱的光弧。
我深吸一口气,松开手掌,将那枚硬币放进路边的流浪汉乞讨碗中。
“叮当”一声轻响。
头也不回地,我走向那束越来越近的光。
工作室的早晨总是从咖啡香开始。
我站在操作台前,用镊子小心地将一颗切割成泪滴形的海蓝宝镶嵌进银质底座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绒布上,宝石内部泛起海洋般的波纹。
“棠姐,有位姓陆的女士找您。”助理小孟推门探头,表情有些犹豫,“她说没有预约,但坚持要见您。”
镊子尖微微一顿。
“请她到会客室。”
会客室里,陆夫人坐在米白色沙发上,依旧是一身香奈儿套装,珍珠项链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和三年前那个雨夜找到我的女人相比,她似乎没有任何变化——除了眼角多出的两道细纹。
“夏小姐。”她将茶杯放回托盘,瓷器轻碰发出清脆声响,“好久不见。”
“陆夫人。”我在她对面坐下,“不知您今天来有何指教?”
她从爱马仕手包里取出一个信封,推到玻璃茶几中央。
薄薄的信封,边缘平整。
我不用打开也知道里面是什么。
“一千五百元。”陆夫人声音平静,像在陈述天气,“夏小姐是聪明人,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沉舟现在执掌整个陆氏集团,他的婚姻关系到家族利益。三年前你们没能在一起,三年后更不可能。”
我拿起信封,指腹能感觉到里面纸币的厚度。
一模一样。
连信封都是同一个牌子。
“陆夫人,”我抬眼看她,“您知道现在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吗?”
她皱眉:“什么意思?”
“三年前,您用一千五百元让我离开您儿子。三年过去了,您还是给一千五百元。”我慢慢撕开信封封口,抽出里面十五张崭新的百元钞票,“陆家的羞辱,倒是很保值。”
陆夫人脸色微变:“你不要不识抬举。当年你能拿钱走人,现在也能。沉舟对你不过是一时兴起,他现在有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人选——”
“林氏集团的千金,林薇薇。”我接过话头,将钞票在手中理齐,“财经新闻上登过两次约会照片。陆夫人安排得很周到。”
“你既然知道,就该明白你们之间的差距。”
“我当然明白。”我将钞票重新装回信封,“所以这钱,我收下了。”
她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干脆,准备好的说辞卡在喉咙里。
“不过,”我站起身,“三年前我收下这笔钱,是为了救我弟弟的命。三年后我收下它,是因为我觉得您可怜。”
“你说什么?”她霍然起身。
“守着旧规则,用旧手段,对付一个您三年前就没能真正赶走的人。”我走到门口,拉开门,“陆夫人,钱我收了,您请回吧。顺便提醒您,下次如果还要做这种事,记得考虑通胀——或者至少,加点价。”
她的脸涨得通红,抓起手包快步离开,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里带着怒气。
小孟探头进来:“棠姐,没事吧?”
“没事。”我晃了晃手中的信封,“下午我们去一趟儿童医院。”
---
市儿童医院的音乐治疗室里,六个孩子围成一圈,跟着老师拍手打节奏。玻璃墙外,我将信封递给基金会负责人王主任。
“一千五百元,捐给音乐治疗项目。”
王主任接过,有些惊讶:“夏小姐,您上周才捐过一批乐器,这……”
“这是额外的。”我看向治疗室里那些因为疾病而苍白的小脸,“就当是某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陆姓人士的善意。”
其中一个戴毛线帽的小女孩看见我,隔着玻璃挥了挥手。她叫朵朵,白血病,父母离异后跟着奶奶生活。上周我来时,她缩在角落不说话,现在居然在笑。
“朵朵最近怎么样?”
“好多了。”王主任眼眶微红,“音乐治疗真的有用。夏小姐,要不是您和几位赞助人,我们这个项目根本撑不下去。”
我摇摇头,没说话。
三年前,我弟弟躺在重症监护室里,每天的医疗费像流水。陆夫人找到我,说只要我离开陆沉舟,她不但会支付所有医疗费,还会请最好的专家。
那时我二十一岁,握着病危通知书,面前是优雅冷酷的陆夫人,手机里是陆沉舟发来的消息:“夏棠,纪念日想去哪里?我订了餐厅,但你想去哪里都行。”
我选了弟弟。
选了那个雨夜里,用最残忍的方式推开陆沉舟。
“棠姐?”小孟轻声唤我。
我回过神:“走吧,下午还要见供应商。”
转身时,我最后看了一眼治疗室。朵朵正敲着一架小木琴,阳光洒在她稀疏的头发上。
至少这一千五,能让她多笑几次。
---
陆氏集团顶楼总裁办公室。
陆沉舟站在落地窗前,俯瞰着脚下的城市。午后阳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投射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。
“陆总,查到了。”特助陈峰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平板,“夏棠小姐三年前离开后,去了佛罗伦萨学习珠宝设计,去年获得国际新锐设计师金奖。三个月前回国,创立个人品牌‘逆光’,目前在业界已有一定知名度。”
“为什么突然回国?”
“据说是为了她弟弟。她弟弟三年前重病,现在已经康复,在国内读大学。夏棠小姐回国后,除了经营品牌,还定期资助儿童医院的音乐治疗项目。”
陆沉舟转过身:“三年前她弟弟重病?”
“是的,白血病,当时情况危急。但后来突然得到一笔匿名资助,请了国外专家,现在已经完全康复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
陆沉舟走到办公桌前,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三年前,夏棠突然提出分手,理由是她“腻了”,说他“太粘人”。他当时不信,追到她租住的公寓楼下,在大雨里站了一夜。
她推开窗,扔下他送的所有礼物,包括那枚他熬夜打工买的求婚戒指。
“陆沉舟,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。”她站在楼上,声音冷得像冰,“像条被抛弃的狗。这样很难看,你知道吗?”
那一刻,他真觉得自己像条狗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陈峰犹豫了一下,“今天上午,夫人去见了夏棠小姐。”
敲击桌面的手指停住了。
“说了什么?”
“具体不清楚。但夫人离开时脸色很不好。夏棠小姐随后去了一趟儿童医院,以匿名方式捐了一千五百元给音乐治疗项目。”
“一千五……”陆沉舟重复这个数字,眼神骤然冷冽。
他想起三年前分手后,母亲轻描淡写地说:“那女孩自己走了。我给了她一点钱,她收得很干脆。沉舟,这种出身的女孩,看上的不过是陆家的钱。”
当时他信了。
因为夏棠走得那么决绝,连一件礼物都没留下。
“陈峰,”陆沉舟声音低沉,“三年前我母亲的账户,查一下支出记录。重点看五到七月,有没有一笔一千五的转账或取现。”
“陆总,这……”
“去查。”
陈峰离开后,陆沉舟走到酒柜前,倒了半杯威士忌。琥珀色液体在杯中摇晃,冰块碰撞杯壁,发出细碎声响。
他想起拍卖会那晚,夏棠下车前说的话。
“破碎的东西也能反射光芒。但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,再亮的光也照不回来。”
当时他只当她是在讽刺。
现在想来,那句话里有别的意味。
手机震动,是母亲发来的消息:“沉舟,今晚林董家的晚宴,记得准时到。薇薇特意从巴黎飞回来,你别让她失望。”
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,放下酒杯。
窗外的城市开始亮起灯火,车流如织。这座城市每天上演无数相遇与离别,大多数故事都悄无声息地结束,像从未发生过。
但有些故事,还没到结局的时候。
陆沉舟拿起外套,走出办公室。
电梯下行时,他对着镜面墙壁整理领带,看见自己眼中久违的光——那种狩猎者锁定目标时的锐利光芒。
夏棠。
他在心中默念这个名字。
三年前你为什么要走,我会查清楚。
而这一次,我不会再让你轻易离开。
周五的傍晚,工作室外的梧桐街被染成金色。
我锁好门,转身时差点撞进一个人怀里。
“抱歉——”话卡在喉咙里。
陆沉舟站在台阶下,黑色衬衫解开了第一颗纽扣,袖口挽到手肘。他就这么看着我,眼神像要把人钉在原地。
“陆总。”我退后半步,“有事吗?”
“一千五百元。”他开口,声音在暮色里显得沙哑,“我妈今天找你了,是不是?”
我握紧手提包:“陆夫人确实来过。”
“你收了钱?”
“收了。”
他短促地笑了一声,那笑声里没有温度:“夏棠,三年不见,你还是这么务实。一千五就能买你离我远点,看来我在你心里也就值这个价。”
晚风吹过,梧桐叶簌簌作响。
我走下台阶,与他平视:“陆沉舟,你知不知道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?”
他眉头皱起:“什么?”
“三年前,你母亲给我一千五,让我离开你。三年后,她还是给一千五。”我往前走,他下意识跟上,“你们陆家的羞辱,不仅保值,还挺念旧。”
街道拐角处有家便利店,灯光温暖。我走进去,从冰柜里拿出一瓶矿泉水,扫码付款。
陆沉舟跟进来,站在我身后。
收银员小姑娘好奇地打量我们,眼神在陆沉舟身上多停了几秒——他确实太显眼,即使穿着便服,也掩不住那股上位者的气场。
“三年前那笔钱,你用来做什么了?”他问。
“花了。”我拧开瓶盖。
“怎么花的?”
“陆总现在是在审问我吗?”我转身看他,“钱给我了,怎么花是我的自由。就像三年前你母亲给我钱,我离开你——交易完成,银货两讫。”
“银货两讫?”他重复这四个字,忽然伸手撑在我身后的货架上,将我困在他与冰柜之间,“夏棠,我们之间从来就不是交易。”
便利店的白炽灯光落在他脸上,我清晰地看见他眼中的血丝。他身上有淡淡的酒气,混合着熟悉的木质香。
“你喝酒了?”
“一点点。”他盯着我,“回答我,三年前为什么要走?真的是为了钱?”
我垂下眼,看着手中水瓶上凝结的水珠:“陆沉舟,过去的事有什么意义吗?你现在是陆氏总裁,有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人选,我也有自己的事业。我们早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。”
“你看着我说。”
我抬起头。
他的眼睛在这么近的距离里,像深不见底的潭。三年前,这双眼睛会因为我的一句话而亮起来,会因为我生病而满是担忧,会在吻我时温柔得让人想哭。
现在里面只有固执的探寻。
“好,我告诉你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真实,“三年前我走,是因为我腻了。你太粘人,占有欲太强,我想要自由。你母亲给的那一千五,不过是顺便。这个答案你满意吗?”
他盯着我,良久,忽然笑了。
不是冷笑,不是嘲讽的笑,而是一种疲惫的、近乎破碎的笑容。
“撒谎。”他轻声说,“夏棠,你撒谎的时候,右手指尖会无意识地摩挲左手腕。”
我一怔,低头看向自己的手。
确实,我的右手拇指正无意识地摩挲着左手腕上的那条银链。
“还有,”他继续道,“你弟弟三年前得了白血病,需要大笔医疗费。我妈找过你,是不是?”
街道上的车流声、便利店的音乐声、远处孩子们的嬉闹声,在这一刻都退得很远。
我张了张嘴,发不出声音。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?”他问,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,“为什么宁可让我恨你,也不告诉我真相?”
“告诉你有什么用?”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,“陆沉舟,三年前你是什么处境?你爸刚去世,你叔伯虎视眈眈,你在陆氏的位置摇摇欲坠。你母亲说得对,那时你自身难保,帮不了我,只会让你更被动。”
“所以你就替我做决定?”
“我做了对我、对我弟弟最好的决定。”我推开他,“事实证明我是对的。你成了陆氏总裁,我弟弟康复了,我们各自都过得不错。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”
“我不觉得这是结局。”他拦住我的去路。
“那你想怎么样?”我抬头看他,“陆沉舟,我们都不是三年前的我们了。你有你的责任,我也有我的生活。那一千五我捐给了儿童医院,如果你觉得不够,我可以还你三千。”
他沉默地看着我,眼神复杂得我读不懂。
良久,他问:“手腕上的链子,为什么还戴着?”
我下意识护住手腕:“习惯了。”
“撒谎。”他又一次戳穿我,“这是我送你的二十岁生日礼物。你说过,如果有一天不爱我了,就把它扔了。”
暮色彻底笼罩了街道,路灯一盏盏亮起。
便利店的光从我们身后透出来,在地上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。
“夏棠,”他声音很轻,“三年来,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。”
我握紧水瓶,塑料瓶身发出细微的嘎吱声。
“陆总,”我听见自己用最官方的语气说,“这种话对林小姐说比较合适。我还有事,先走了。”
这一次他没有拦我。
我快步走向街口,拦下一辆出租车。上车前,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陆沉舟还站在便利店门口,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低着头,看不清表情,整个人浸在昏黄的光里,像一尊沉默的雕像。
车子启动,他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。
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:“小姐,你没事吧?”
我抬手抹了把脸,才发现自己哭了。
真没出息。
三年了,我以为自己已经刀枪不入,却还是会被他一句话击溃。
手机震动,是小孟发来的消息:“棠姐,下周三新品发布会的场地确认了,在洲际酒店宴会厅。另外,刚收到邮件,我们入选了年度新锐品牌大奖的最终名单!”
我擦干眼泪,回复:“收到,辛苦。”
窗外,城市华灯初上,每一扇亮着的窗户后都有一个故事。大多数故事平淡如水,有些故事痛彻心扉,极少数的故事能在破碎后重生。
我不知道我和陆沉舟的故事属于哪一种。
但我知道,无论属于哪一种,我都得继续往前走。
就像我设计的“逆光”系列——破碎的晶体依然可以反射光芒,裂痕本身也能成为风景。
“师傅,”我对司机说,“去儿童医院。”
我想去看看朵朵。
看看那些在病痛中依然努力微笑的孩子。
他们会提醒我,这个世界除了爱情,还有很多值得为之努力的事情。
比如活着。
比如让更多人活着。
那场雨下得真大。
我坐在弟弟夏阳的病床旁,握着他瘦得只剩骨头的手。监护仪的滴答声像倒计时,窗外是倾盆大雨,雨水在玻璃上划出扭曲的痕迹。
“姐,”夏阳闭着眼睛,声音轻得像羽毛,“我是不是要死了?”
“胡说。”我擦掉他额头的汗,“医生说新方案很有效,很快就能好。”
他在撒谎。医生半小时前才跟我说,如果下周还找不到匹配的骨髓,如果感染继续恶化,如果——
门被轻轻敲响。
陆夫人站在门口,一身香奈儿套装纤尘不染,与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格格不入。她示意我出去谈。
走廊尽头,她开门见山:“夏小姐,沉舟为了你,拒绝了他父亲安排的联姻。现在他父亲病重,他叔伯都在争权,这个时候他不能有任何弱点。”
我靠着冰冷的墙壁:“所以我是他的弱点?”
“感情是。”她看着我,眼神里没有温度,“特别是你这样的女孩,家境普通,还有个重病的弟弟。这在陆家那些老人眼里,就是可以被攻击的软肋。”
“陆夫人到底想说什么?”
她从手包里取出一个信封:“一千五百元。离开沉舟,立刻,现在。”
我盯着那个信封,喉咙发紧。
“如果你答应,”她继续说,“我会联系最好的血液科专家,承担你弟弟所有的医疗费,包括后续康复。如果不答应——”她停顿一下,“这家医院是陆氏投资的。我可以让你弟弟明天就出院。”
雨声敲打着窗户,像无数细小的鼓点。
“沉舟知道吗?”我问。
“他不知道,也不能知道。”陆夫人语气坚决,“他如果知道真相,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帮你。但那样他会失去陆氏继承人的位置,你会毁了他。”
监护仪的滴答声在我脑海中回响。
夏阳苍白的脸。
陆沉舟昨晚发来的消息:“夏棠,我爸情况不好,这几天可能没法陪你。等我处理好家里的事,我们好好过纪念日,好吗?”
他连自己都顾不上,还在想着我。
“我给你三分钟考虑。”陆夫人看了眼腕表。
我看着窗外的大雨,想起三天前,陆沉舟在我家楼下,举着伞等我下楼。伞大半倾到我这边,他半个肩膀都湿了,却笑着说:“夏棠,等我们老了,我就这样每天接你下班。”
那时我以为,我们真的有未来。
“我答应。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,陌生而平静,“但我需要时间,三天。三天后,我会跟他分手。”
陆夫人把信封放进我手里:“聪明人。记住,不能让沉舟知道真相,否则协议作废。”
她高跟鞋的声音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我握着那个信封,纸边割得掌心生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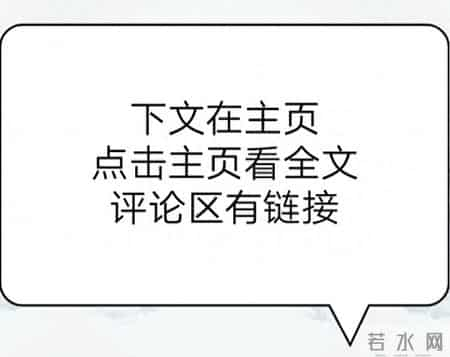
本文标题:(完)三年前,总裁母亲用一千万让我离开总裁
本文链接:http://www.gzlysc.com/life/3569.html
声明: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采集网络资源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本站删除。






